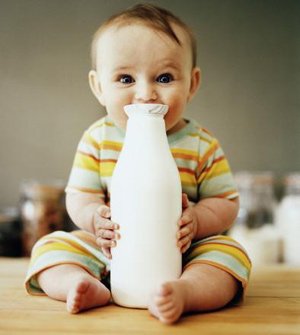張守仁:在文學的黃金歲月中“刻舟求劍”
被譽為北京文壇“四大名編”之一的張守仁親身經歷了文學刊物繁榮發展的一段激情燃燒歲月,1978年8月,他與其他兩位同事一起創辦了《十月》雜志,半年后上海的《收獲》雜志復刊,一年以后《當代》雜志創刊,一年半以后南京《鐘山》雜志創刊……隨后大概有十幾家刊物開始像雨后春筍般出現。此后的40年間,他和當代作家們接觸漸深,并逐漸成為摯友、諍友。因常年習慣用日記記錄點滴,如今,他將這些往事、回憶集結成集,著成《名作家記》。“寫下長達四十多年的編輯憶舊,記下新時期黃金歲月中旗幟性刊物《十月》的風采,錄下作家們的音容笑貌、情感歷程、生活細節,不讓它們湮滅于歷史塵埃之中。這是我晚年必須做的事,也算是我這個老編輯留存給讀者的一份薄禮吧。”
14日,在《名作家記》新書發布會上,作家寧肯、周曉楓,《光明日報》文藝部主任彭程,以及該書作者張守仁,一同回溯、暢談了新時期文學的黃金歲月。
“守仁老師是一位和善而頑強的編輯,他用他的學問和蔫蔫兒的堅持性征服了作者,他不吵鬧,不神吹冒泡,也不是‘萬事通’、‘見面熟式’的活動家,但是他具有無堅不摧的能力”。著名作家王蒙曾這樣評價張守仁。在周曉楓眼里,張守仁“無堅不摧”的能力體現在犀利的“眼力”和勤奮的“腳力”上。“無論是普通群眾來稿還是多年不搞創作的作家,抑或剛剛萌芽的新人,他都能在各種各樣的作家里發現好稿子。他還非常勤于和作者建立聯系,甚至上門拜訪,對作家的創作進度十分上心,這些令他和作家的關系特別好。”
從張守仁的文字中,周曉楓再一次重新回到那些珍貴的時刻,如史鐵生最后捐獻自己的器官、張賢亮曾因假死被送往太平間……那個時代,編輯會參與到作家、作品的成長中,這些都是有溫度的回憶。周曉楓將寫作比喻為“刻舟求劍”,光陰如水,很多過去的經歷、活力、激情都會像劍一樣掉到水里,留下的都是有傷痕的刻痕,但是只有刻痕才會讓人銘記于心。劍或許在生活中會生銹,但在文字中卻永遠不會。“我覺得張守仁就是刻舟求劍的人,他用他的執著、熱情、勤奮,在整個編輯生涯中留下可以尋找瞬間的一道道刻痕。”
周曉楓談到,在當下時代,出書的人越來越多,身份也很駁雜,可能有名家,也有新人,有媒體英雄,也有網絡紅人,很多年輕編輯來不及“孵化”跟作家的感情,他們的身份越來越具有工具化和服務性。她希望青年編輯能從這本書中看到,一名優秀的編輯是如何將對文學的熱愛貫穿到工作中。“如今張老師每發現一位新人、一個優秀的作者,就和晚年得子一樣,手舞足蹈,興高采烈,這種對文學永不褪色的激情令人動容。”
彭程的第一篇文章是張守仁所編發,其后發表的很多篇作品,張守仁都會針對選題、角度、結構等方面提出建議和指點。在他的心里,張守仁對于新人的提攜和發現不遺余力。無論是當年已嶄露頭角的王蒙、剛創作《高山下的花環》的李存葆、還是初出茅廬的葦岸, 王守仁在與很多作家的交往中都秉持著“吾愛吾師,吾更愛真理”的原則,君子之交淡如水,真摯而不諂媚。在書中,他對筆下的作家滿懷感情,呈現出這些作家鮮明生動的性格,頗具“立體感”。
彭程談到,《名作家記》收錄的40多篇文章,講述了張守仁與近40位作家的交往經歷,每每細讀都不由得發出會意微笑。他用“夜語”這個詞概括張守仁的編輯生涯,“我記得他的前言中有兩句詩,叫‘當時共我夜語人,點檢如今無一半’。這是一個很有表現力的詞匯。”他還談到,無論文學界出現哪些新的現象、新的流派、新的表現形式,張守仁都非常熟悉。如果遇到自己不太了解的事物,他就主動去打聽、隨時借閱了解。在彭程看來,這一切都源自張守仁對文學的熱愛。
寧肯則從書中看到了“擔當性”。作家創作需要研究社會,研究時代,編輯也需要研究,甚至要和作家站在相同位置上思考問題,此外還要有憂患意識、悲憫意識、批判意識、承擔意識。“張守仁老師之所以能夠發現很多有分量的作品,根本在于他對社會敏感度和社會問題的深刻把握”。
張守仁回應到,自己并不是起點很高的編輯,靠著持之以恒的學習和勤能補拙的精神,才有了今天的成就。“作為一名編輯要有責任感,要虛心向每一個人學習。我接觸的每一個人都是我的親人,我要向他們學習。今天幾位作家的談話都是溢美之詞,我僅僅是新時期文學黃金歲月的記錄者,如此而已。”(李菁)
- 標簽:
- 編輯:馬可
- 相關文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