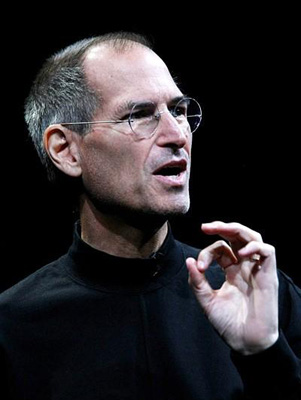劉澤華:傳統(tǒng)政治思維的陰陽組合結(jié)構(gòu)
中國古代思想的一個重要現(xiàn)象是“混沌”,呂思勉先生在《文史通義評》中曾有論述。張岱年先生在《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》文中指出,中國幾千年來文化傳統(tǒng)的基本精神其缺陷之一就是“混沌思維”。所謂“混沌”,就是思想概念、范疇的界定與運用,沒有嚴密的區(qū)分。對這種現(xiàn)象中外學(xué)者都有過論述。
說混沌,其實也不是混沌一片,細分還是有其理路的,至少在政治思想中是如此。其理路就是陰陽組合結(jié)構(gòu)。多年以前我曾說過:“我認為中國傳統(tǒng)政治思想在其學(xué)理上是很難找出理論元點的,各種理論命題是交織在一起的,以往我們有時稱之為‘混沌性’,有時稱之為‘陰陽結(jié)構(gòu)’,有時稱之為‘主輔組合命題’等。”也就是說,在我看來,說“混沌”還只是表征,尚待更深入分析。于是提出了“陰陽結(jié)構(gòu)”,“陰陽組合命題”或“主輔組合命題”。
在傳統(tǒng)政治思想中,我們的先哲幾乎都不從一個理論元點來推導(dǎo)自己的理論,而是在“陰陽組合結(jié)構(gòu)”中進行思維和闡明道理。這里不妨先開列一些具體的陰陽組合命題,諸如:天人合一與天王合一;圣人與圣王;道高于君與君道同體;天下為公與王有天下;尊君與罪君;正統(tǒng)與革命;民本與君本;人為貴與貴賤有序;等級與均平;納諫(聽眾)與獨斷;思想一統(tǒng)與人各有志;教化與愚民;王遵禮法與王制禮法;民為衣食父母與皇恩浩蕩、仰上而生……我開列了這一大串,為了說明這種組合命題的普遍性。這里用了“陰陽組合結(jié)構(gòu)”,而不用對立統(tǒng)一,是有用意的。在上述組合關(guān)系中有對立統(tǒng)一的因素,但與對立統(tǒng)一又有原則的不同,對立統(tǒng)一包含著對立面的轉(zhuǎn)化,但陰陽之間不能轉(zhuǎn)化,特別是在政治與政治觀念領(lǐng)域,居于陽位的君、父、 夫與居于陰位的臣、子、婦,其間相對而不能轉(zhuǎn)化,否則便是錯位。因此陰陽組合結(jié)構(gòu)只是對立統(tǒng)一的一種形式和狀態(tài),兩者不是等同的。我上邊羅列的各個命題,都是陰陽組合關(guān)系,主輔不能錯位。比如在君本與民本這對陰陽組合命題中,君本與民本互相依存,談到君本一定要說民本;同樣,談到民本也離不開君本,但君本的主體位置是不能變動的。下邊就兩個組合命題稍作說明,以示其概。
先說“道高于君與君主體道”的組合。“道”是中國傳統(tǒng)思想文化的核心范疇之一,是理性(也包含程度不同的神性)的最高抽象,又是整個思想文化的命脈。
“王”是最高權(quán)力者的稱謂,同時又代表著以專制權(quán)力為中心的社會秩序以及與這種秩序相對應(yīng)的觀念體系。
道與王是什么關(guān)系?就我拜讀過的論著,特別是新儒家,十分強調(diào)儒家的道與王是二分的,常常把“道高于君”、“從道不從君”作為理論元點來進行推理,認定道是社會的獨立的理性系統(tǒng),由儒生操握,對王起著規(guī)范、牽制和制約作用。就一隅而論,足以成理;然全面考察,則多偏頗。在我看來,道與王的關(guān)系是相對二分與合二而一的有機組合關(guān)系,分中有合,合中有分,分合相輔,以合為主。這不限于儒家,而是整個傳統(tǒng)思想文化中的主干。
“道高于君”、“從道不從君”只是組合命題一面,還有更重要的一面,這就是“君主體道”、“王、道同體”、“道出于王”。
先秦諸子把圣人、君子視為道之原,同時又認為先王、圣王也是道之原。在這一點上先秦諸子沒有分歧,可以說是共識。這一理論為王與道一體化,以及道源于王鋪平了道路。秦始皇是歷史上第一位把自己視為與道同體、自己生道的君主。秦始皇宣布自己是“體道行德”,實現(xiàn)了王、道一體化。“體道”這個詞最早見于《莊子·知北游》。其后荀子說:“知道察,知道行,體道者也。”韓非進一步提出“體道”是君主有國、保身之本。秦始皇的“體道”便是由此而來。秦始皇不僅體道,又是圣王,他頒布的制度、命令是“圣制”、“圣意”、“圣志”,永垂萬世。先秦諸子創(chuàng)造的巍巍高尚的“道”一下子變成了秦始皇的囊中之物。秦朝雖然很快垮臺了,秦始皇的思想?yún)s流傳給后世。其后,賈誼提出“君也者,道之所出也。”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·王道》中說:“道,王道也。王者,人之始也。”他還有人所熟悉的“王道通三”之說。道、王道、王混為一體,道由王出。于是李覯竟說出這樣的話:“無王道可也,不可無天子。”在中國的歷史上,人們盡管可以把道捧上天,但一遇到“圣旨”,它就得乖乖讓路。在漫長的年代里,帝王既要搞朕即國家,又要搞朕即道。
宋、明理學(xué)家高揚道統(tǒng)的大旗,道統(tǒng)儼然獨立于王之外。然而恰恰在把道統(tǒng)說得神乎其神的同時,卻又把這個神圣的道敬獻給帝王,這一點在謚號中表現(xiàn)得尤為突出,諸如“應(yīng)道”、“法道”、“繼道”、“合道”、“同道”、“循道”、“備道”、“建道”、“行道”、“章道”、“弘道”、“體道”、“崇道”、“立道”、“凝道”、“明道”、“達道”、“履道”、“隆道”、“契道”、“闡道”、“守道”等詞。漢語詞匯實在太豐富了,在這里,都說明一個問題:帝王是道的體現(xiàn)者。
王對道的占有,或者說道依附于王,是整個傳統(tǒng)思想文化的一個基本命題,幾乎所有的思想家,甚至包括一些具有異端性質(zhì)的人,都沒有從“王道”等大框框中走出來。只要還崇拜“王道”等,那么不僅在理論上被王制和王的觀念所錮,而且所說的道也是為王服務(wù)的。
其實,王對道的占有只是問題的一面,另一面更應(yīng)注意道本身的王權(quán)主義精神。在思想史中有一個重要的事實,即人們在闡發(fā)、高揚“道”的觀念過程中,一直向“道”注入王權(quán)主義精神。進而言之,道的主旨是王權(quán)主義。這一點被我們的許多學(xué)者,特別是被新儒學(xué)所忽視。只要稍稍留意觀察,這一事實應(yīng)該說是昭然的。
中國傳統(tǒng)思想文化中的道無所不在,千姿百態(tài),但影響最大、最具有普遍性的,要屬有關(guān)宇宙結(jié)構(gòu)、本體、規(guī)律方面的含義了。 正是在這種形而上學(xué)的意義中給予王以特殊的定位。《易·系辭上》說:“一陰一陽之謂道。”陰陽相交而生萬物,而君臣尊卑之位便是宇宙結(jié)構(gòu)和秩序的一環(huán)。被形而上學(xué)化的倫理綱常的首位就是君主關(guān)系。程頤說:“天地人只一道也。才通其一,則余皆通。”“道之大本如何求?某告之以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,于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。”朱熹說:“三綱五常,天理民彝之大節(jié),而治道之本根也。”又說:“道之在天下,其實原于天命之性,而行于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之間。”儒家所論的倫理綱常無疑比具體的君主更有普遍意義,甚至經(jīng)常高舉綱常的大旗批判某些君主,有時還走到“革命”的地步。然而這絲毫不意味著對君主制度的否定,恰恰相反,而是從更高的層次肯定了君主專制制度,用形而上學(xué)論證了君主制度是永恒的。我們不能忽視儒家的綱常對王的規(guī)范和批判意義,同時也不宜忽視這種規(guī)范和批判的歸結(jié)點是對王權(quán)制度的肯定。張揚儒學(xué)的朋友對此實在有點漠視,或視而不見,真不知其可也!
道、王相對二分與合二而一是有機組合關(guān)系,同時也形成一種思維范式,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都沒有從這種范式中走出來。這種思維范式的影響比具體內(nèi)容的影響更為廣泛和深遠。
再說“民本與君本”的組合。“民本”與“君本”是中國古代政治思維的兩大基點。歷代思想家、清醒的帝王和政治家都把“君為民主”與“民惟國本”兩大命題相提并論,并在理論上形成穩(wěn)定的“陰陽組合”結(jié)構(gòu)。
“君為民主”把君奉為政治的最高主宰,這是講君權(quán)的絕對性;“民為國本”承認民之向背對政治興敗具有最終決定作用,這是講君權(quán)的相對性。依照邏輯推理,這兩者是不能共容的。如果把“民為國本”視為最高的理論元點,就應(yīng)否定“君為民主”的思路,進而賦予民眾政治權(quán)利,以民主方式選舉國家元首并設(shè)計必要的政治程序以制衡其權(quán)力。可惜,中國古代一切民本論者都沒能從君為民主、治權(quán)在君、君為政本的思路中走出來,從而躍入民主主義范疇。這就注定了“民為國本”命題是“君為民主”命題的附庸,重民的主體是君主,民眾只是政治的客體,民是君主施治、教化的對象,其中并沒有“民治”的思想。這種“民本論”所導(dǎo)出的僅僅是統(tǒng)治者的得民之道、保民之道、治民之道。民本的最終歸宿是實現(xiàn)君本。
“民惟邦本”與“君為政本”,“民貴君輕”與“君尊民卑”,“君以民為本”與“民以君為主”,從平面上看是相對的。如果置入“陰陽結(jié)構(gòu)”中,而兩者各得其位,中國古代政治思維巧妙地將二者圓融在同一理論體系之中。這種思維方式和理論結(jié)構(gòu)注定了民本論同時具有尊君、罪君雙重功能。在這個結(jié)構(gòu)中,罪君不是要改革君主制度,而是乞求清明的君主降臨人世。
“陰陽組合結(jié)構(gòu)”無疑是我們的概括,但其內(nèi)容則是古代政治思維的普遍事實,這種結(jié)構(gòu)性的思維應(yīng)該說是極其高明的,它反映了事務(wù)的對立與統(tǒng)一的一個基本面。也可以說是“中庸”、“執(zhí)兩用中”思想的具體化。這種“結(jié)構(gòu)”的思維方式和認知路線對把握事務(wù)非常有用,也非常聰慧,正是所謂的“極高明而道中庸”。20世紀80年代初,我在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一書中曾用“邊際平衡”來分析和說明孔子的“中庸”思想,應(yīng)該說“陰陽組合結(jié)構(gòu)”把“邊際平衡”更具體地揭示出來了。就思想來說,這種結(jié)構(gòu)的容量很大,說東有東,說西有西,既可以把君主之尊和偉大捧得比天高,但又可以進諫批評,乃至對桀紂之君進行革命。由于有極大的容量,以至于人們無法從這種結(jié)構(gòu)中跳出來,至少在政治思想史范圍內(nèi),直到西方新政治思想傳入以前,先哲們沒有人能突破這種陰陽組合結(jié)構(gòu)。最杰出的思想家黃宗羲雖有過超乎前人的試跳,但終歸沒有跳過去。
在政治實踐上,這種陰陽組合結(jié)構(gòu)的政治理念具有廣泛的和切實的應(yīng)用性。以古代的君主專制體制為例,一方面它是那樣的穩(wěn)固,不管有多少波瀾起伏,多少次改朝換代,這種體制橫豎巋然不動;另一方面,它有相當寬的自我調(diào)整空間和適應(yīng)性。我想這些應(yīng)該說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政治思維的陰陽結(jié)構(gòu)及其相應(yīng)的政治調(diào)整。
這種思維定式影響至深,在我們現(xiàn)實生活中還廣泛流行, 依然籠罩著許多人的思維。如果我們不從這種陰陽組合結(jié)構(gòu)中走出來,我們就不可能登上歷史的新臺階。
原載:《南開學(xué)報:哲社版》2006年第5期
","typetext"}],"- 標簽:
- 編輯:馬可
- 相關(guān)文章